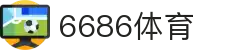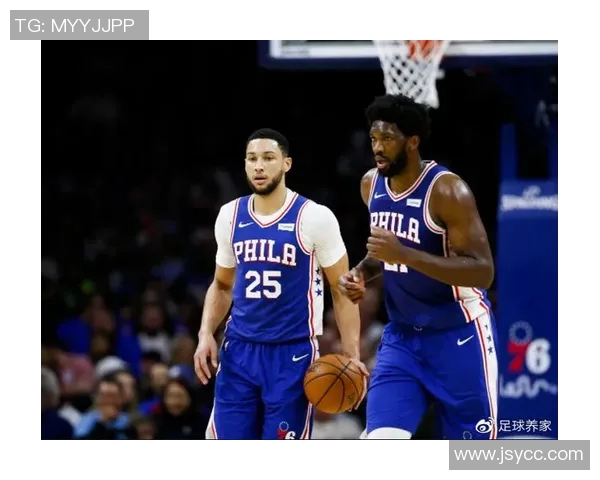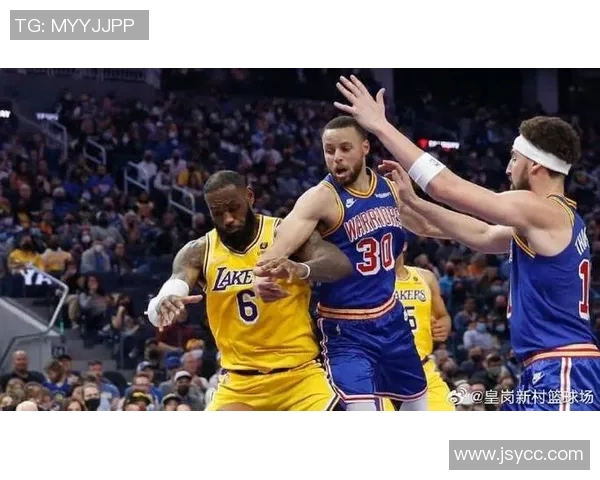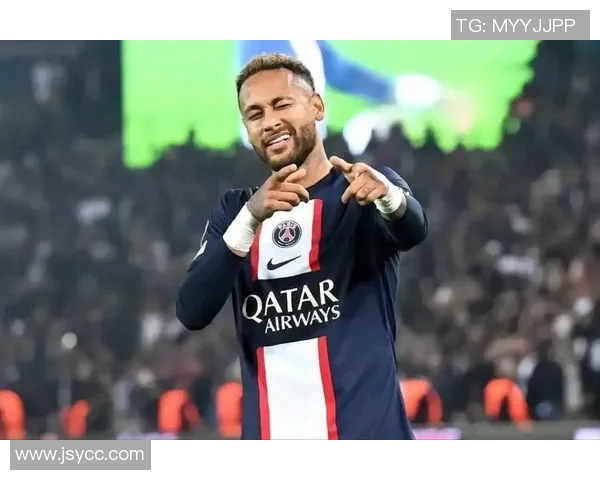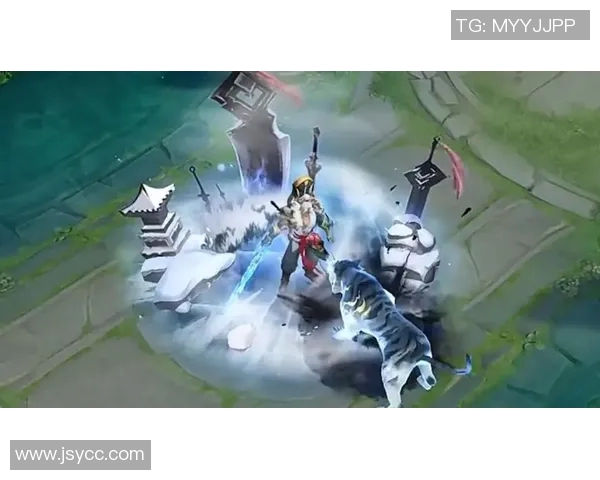1996年的夏天,地里的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。那天傍晚,我妈从田里回来,身后跟着一个陌生女人。那女人穿着一件褪色的碎花衬衫,脸色苍白,却掩不住清秀的眉眼。她赤着脚,裤腿上沾满泥点,像是走了很远的路。我妈递给她一个烤红薯,她接过时手指微微发抖,低声说了句“谢谢”,声音轻得像玉米叶的沙沙声。
玉米地里的相遇
1996年夏天,玉米秆子比人还高。我妈穿过密密的青纱帐时,听见断断续续的呜咽。拨开层层叶片,一个穿碎花裙的年轻女人蜷在田埂上,头发凌乱,脸上挂着泪痕。她抬头时,我妈愣住了——皮肤白净,眉眼清秀,像个城里姑娘。女人怯生生抓住我妈的衣角,手心全是泥。夕阳把玉米叶染成金黄,她手腕的银镯子闪着微光。
短暂的温暖与不安的预感 女人安静地坐在炕沿,灯光映着她清秀的侧脸。她小口吃着玉米饼,偶尔对我露出浅笑。母亲翻出旧棉袄给她披上,屋里难得有了暖意。可当我递6686体育热水时,发现她手腕布满深浅不一的伤痕。她迅速拉紧袖口,眼神闪过惊慌。窗外风声渐紧,她不时望向漆黑院门,手指绞着衣角发白。深夜听见她压抑的啜泣,像被什么追赶着。

突如其来的死亡与未解的谜团
清晨,母亲发现她躺在土炕上已没了呼吸。身体冰冷僵硬,面容却异常安详。邻居们围在院外议论纷纷,有人说她夜里咳得厉害,有人低语她手腕有浅浅的淤青。派出所民警做了简单记录,判定是突发疾病。母亲翻遍她随身布包,只找到半块干馍和一张模糊的照片。那照片上的小男孩笑着,背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“盼归”。女人被草草葬在后山,她的身世随黄土掩埋,只剩老槐树下那座孤坟在风里沉默。